泥哨传情 乡音最亲
笔者在豫东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长大,小时候喜欢玩一种叫泥哨的玩具。后来,随家人移居城市,便再也没有见过泥哨了。
今年春节期间,我遇到了儿时的玩伴,他说他任教的学校请村里的韩大爷给孩子们上过几次吹泥哨的课外兴趣班,孩子们非常喜欢。前不久,我特意回村探访了韩大爷。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那天回村时,恰好遇到韩大爷在给孩子们上泥哨课。全班五十多名学生,人手一个泥哨,全都捧在嘴边,吹得不亦乐乎。
下课后,我拿起一个泥哨细看,它差不多和麻雀一样大,造型也很像一只小鸟。我问韩大爷到学校授课的缘起,韩大爷笑呵呵地说:“学校校长就是咱们村的,他知道我会吹泥哨,就让我来给孩子们上音乐课。感谢学校给我提供的这个机会,这好歹是一门手艺,孩子们愿意学,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学校的一位老师说,泥哨作为一种民间乐器,失传了很可惜,他们请韩大爷来上了几次课,孩子们都很感兴趣。等天暖和了,还准备请韩大爷开设泥哨制作课,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得知我小时候也喜欢吹泥哨,韩大爷邀请我去他家看看。来到韩大爷家,他搬出一个纸箱,里面竟有半箱子泥哨,一个个憨态可掬,十分有趣。韩大爷说,做泥哨对原材料有一定的要求,需到黄河边挖上好的胶泥。我拿起一只泥哨,这与我小时候吹的两孔、三孔的不一样,上面有九个孔。韩大爷告诉我,这些都是经过改进的,九孔的泥哨能吹出七个音,只要变换气力和指法,便可吹出多种悦耳动听的旋律。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泥哨居然没有模具,全是韩大爷手工捏制的。制作泥哨的工具很简单,就几根长短不一的竹签,几把厚薄不同的刀片。韩大爷说,因为音有高低、长短、粗细之分,孔也得凿得大小、厚薄、方圆不同,这对力道有很高的要求。接下来,还要晾干、修补、烧制、打磨、试音……
这时,韩大爷的老伴儿走了过来,说:“这东西已没多少人稀罕了,可他就是捏得上瘾。去年冬天,还跑到黄河边去取土,也不怕给冻出毛病。”老伴的话,有嗔怪,也有心疼。
韩大爷笑着说:“泥哨救过俺一家人的命,连她也是俺用这小玩意儿哄来的。”
说起来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韩大爷制作泥哨的手艺是父亲手把手传给他的,他也算出身泥哨世家了。可一开始,因为年龄小、贪玩,他并不喜欢这种土里土气的小玩意儿。吹吹玩玩还行,真要又挖土又和泥、又晾晒又凿孔、又烧制又打磨地动手制作,再一个一个地试音、修复、兜售,他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
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村里的人都走光了,七八岁的他跟着父母逃荒到山西绛县。正是那次经历,让他知道会一门手艺是多么重要。逃荒路上,全家人要靠乞讨果腹。可他破衣烂衫的,跟个野孩子一样,每次都讨不到东西。而他父亲凭借吹泥哨的绝活儿,总能讨到些红薯或窝窝头。
一天,他看到路边有户人家,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央求给点吃的。结果,被赶了出来。后来,他父亲上门给人家吹奏了一曲,那户人家给了一碗热面汤。他流着泪喝完了那碗汤,当时,父亲对他说:“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即使要饭也得会一门手艺。用手艺要饭,不用那么低三下四。”这句话,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
到了绛县后,他们一家人在一个小山村的破庙里住了下来。他父亲发现那里的土质好,可以制作泥哨,就带着他和他母亲捏泥哨。捏了卖钱,或是换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到十五六岁时,韩大爷不仅可以用泥哨吹奏多种曲子,也成了捏制泥哨的能手。
有一次,他在山坡上给泥哨试音,动听的哨声吸引到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后来,小姑娘经常来听他吹哨。再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天,韩大爷吹奏了《达坂城的姑娘》和《遇上你是我的缘》,韩大妈听得抿着嘴乐。时光荏苒,当年那个与他因哨结缘的小姑娘,如今已是与他白头偕老的老伴儿了。
哨小故事多,曲短日月长。有这些割舍不下的情结,难怪韩大爷会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地给学生们开设泥哨课了。而今,泥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可还有一个老人对它不离不弃,有一群孩子与老人琴瑟和鸣。这称得上是另一段佳话了。
说来有些遗憾,我还没看到那个新捏的泥哨凿出完整的九个孔来,天就黑下来了。我起身告辞,韩大爷吹着《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把我送到村口。
泥哨传情,乡音最亲。据说听觉也有乡愁,这哨声果然神奇,唤起了我许多儿时的记忆,导引着一股暖流流遍全身。
(图为制作泥哨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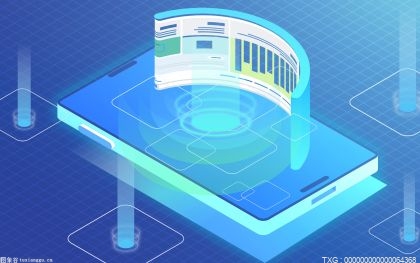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