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下坠的悬浮剧,为何还能不断“上新”? 全球快看点
作者:曹晓华
女性群像剧的经典IP《欢乐颂》系列第四季,在长达37集的剧情“拉扯”中迎来“悬而未决”的大结局。五位女性的故事都只有个阶段性的交代,而《欢乐颂5》的预告片已经迫不及待地招揽起生意,希望观众还有耐心听她们下回分解。
去年夏天以“新五美”主演阵容面世的《欢乐颂3》收获了一波差评,牵强附会的姐妹情谊极具“塑料感”。即便如此,随着女性题材电视剧近年来的全面开花,“欢乐颂”IP显然还有其“剩余价值”。人们对于女性就业、生育、个人成长、原生家庭影响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为相关的议题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也为贴满“女性标签”的影视剧带来了可观的市场红利。女性的现实困境反而成为持续盈利的素材,这的确能够部分解释,为何口碑急剧下滑的“欢乐颂”IP如此急不可耐地连续推出打磨欠周的续集。与此同时,观众与电视剧达成的一些“无奈默契”,也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资本。
 (资料图)
(资料图)
或许,从“新五美”里最不讨喜的何悯鸿身上,就可以看到女性的现实困境是如何被转换为自我排解的荧屏镜像。
从“五美俱美”到“四对一”
在《欢乐颂》第一、二季中,安迪、曲筱绡、樊胜美、关雎尔和邱莹莹都有各自的职场、生活和情感烦恼。五人的故事线既可以做到“花开数朵,各表一枝”,又相互穿插影响,五位女性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最后达成了“五美俱美”的结局。“欢乐颂”IP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五美各有所长,虽然不会是永远的“人间清醒”,但也不会一直“鬼迷心窍”。立体丰满的人物加上女性题材热度渐起,《欢乐颂1》的热播在女性群像剧系列中可谓占得先机,即便之后的《欢乐颂2》口碑略有下滑,但观众依然愿意为“五美”情怀买单。显然,第三、四季想趁热打铁,继续挖掘这一IP的价值,然而只挖掘不发展,注定只是竭泽而渔。
在第三季中就饱受争议的文学编辑何悯鸿,本就被“白莲花”“圣母”“双标”“眼高手低”等负面评论包围,在第四季中继续走出被心机男友轻易PUA的“黑红”路线。曾经的“五美”小团体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变成了“四拖一”模式,比起双商极高的白富美科研人员叶蓁蓁、果敢独立揭发上司性骚扰的职场精英方芷衡、高职学历一路打拼到国际酒店客房部经理的朱喆和刀子嘴豆腐心的技术员余初晖,初入职场的何悯鸿显得“执拗”又“无能”。面对朋友们的循循善诱,她在为人处世中的“道义坚守”不仅让其丢了工作,也得罪了欢乐颂的姐妹。她在失业后不慎受到戚牧的情感控制,“孤傲而决绝”地与四个“一斤心眼子”的欢乐颂朋友绝交,与苦口婆心的家人也断绝了关系。
这种“四拖一”的模式简单化了人物关系,也划分出两个别扭的阵营,以能力超强的四美衬托“有百害而无一用”的何悯鸿,激化了人物间的矛盾,也使误入歧途的何悯鸿显得不可理喻。当观众无法和何悯鸿共情的时候,人物就变成了一个毫无逻辑可言的“箭垛”,无论是初出茅庐的上班族还是入职多年的职场老油条,都可以肆意向何悯鸿放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欢乐颂IP的倒退,就是省却了“哀其不幸”的铺垫,凸显不合理的无脑人设,观众只需与其他四美共情,进行“怒其不争”的发泄。
只是,在女性群像内部分裂出“四对一”的模式,是必要的吗?
我们为什么讨厌何悯鸿?
“新五美”的人设多少带着“老五美”的影子,比如初次登场时强势又冷淡的职场精英方芷衡,心里默默背负着过去的隐痛,与安迪颇为相似;原生家庭极为糟糕的朱喆和余初晖,总是要和自己的家人斗智斗勇,这与樊胜美的经历有所重合;叶蓁蓁和曲筱绡都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出手阔绰,可以轻易用钱解决问题。按照这样的排列组合,何悯鸿则是综合了邱莹莹的鲁莽新手和关雎尔的乖乖女形象,一开始的人设就是需要被引导、被纠正的菜鸟,同时作为麻烦制造者不可避免地被嫌弃。
如果说在第三季中多少还保留着五位女性从陌生人到好朋友的共同成长式叙事模式,那么到了第四季随着小团体阵营分裂成“四对一”,观众自然代入面对各种麻烦攻无不克的四美阵营,嘲笑何悯鸿“胸怀星辰大海,眼前常识不通”。叶蓁蓁霸气回应实验室里的流言蜚语,方芷衡靠自己多次摆脱李勋妻子的纠缠并赢得了同行的尊重,朱喆与只知索取的原生家庭一刀两断,余初晖则帮助母亲逃脱了家暴成瘾的父亲。反观何悯鸿,执拗地落入上级的圈套,被迫离职,为落入戚牧的控制作了铺垫,在卖文谋生的日子里需要室友提点如何做饭节省伙食费,面对一拖再拖的稿费选择降低费用受尽委屈,未婚先孕甚至需要室友提醒买验孕棒。与此同时,她又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看待欢乐颂姐妹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建议显得与现实脱节,而自己遭遇问题时又躲在姐妹身后,把麻烦和危险推给无辜的朋友。
比起八面玲珑可以独自应对困境的朱喆和余初晖、学识过人又自带“钞能力”的叶蓁蓁、业务能力过硬还练了多年拳脚的方芷衡,何悯鸿就是一个社会化失败的巨婴。巨婴的坚守,自然毫无价值。
于是,《欢乐颂》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事后诸葛亮”,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失误、挫折、懊悔和痛苦,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无助和无奈,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
是谁在为悬浮剧“续命”?
我们已经习惯眯着眼睛看荧屏上打扮精致摇着红酒杯的红男绿女,不管他们在剧中的身份是打工人还是管理层,都在滤镜美颜下发白发光发亮,高级公寓这种在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奢侈享受,在职场剧中成了人设的刚需。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一再被批评“悬浮”,在抓舆论热点和蹭话题热度方面,剧集的宣发从不拉胯,甚至可以说十分接地气,女性的事业、家庭、情感一个都不能少。有话题就有流量,有流量就有变现的无限可能。于是,女性题材悬浮剧带着议题的热度护体,走上了爆发式生产的捷径,各个年龄段的大女主形象甚至快要溢出屏幕。
然而,以“酷霸拽”的爽文设定来“悬空”讨论女性现实问题,对荧屏外的观众意义几何?《欢乐颂》IP自然也不能免俗,即便是颇受好评的第一季,悬浮的设置也比比皆是,只是经过多年的“打磨”,到了第四季,观众失望地发现,非但剧中的人设不能有所突破,连叶蓁蓁的那袋橘子都变白了,并且磨了皮。
戚牧接近何悯鸿,逐个离间她与欢乐颂姐妹的关系,骗取她无条件的信任,直至何悯鸿未婚先孕,顺水推舟提出结婚,将其带到寒酸的出租屋,逼走保姆,让何悯鸿“甘之若饴”地照看重病的母亲。这条故事线显然是对PUA精神控制教科书般的展示,但是经由“箭垛”人物何悯鸿展现出来,加上其他四美的衬托,竟有何悯鸿“自讨苦吃”“自作自受”的观感。而戚牧和母亲租住的老破小,又十分“写实”地体现出戚牧作为一个外表光鲜的白领,承受着实际生活的不堪。都市打工人的真实处境竟然通过一个操纵女性的反面形象反映出来,而收入还不及戚牧的几位女性角色,即便身处各种麻烦,经济上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还能在环境雅致的高档住宅中相互串门,其乐融融。戚牧及其身后老破小张牙舞爪的“真实”,只用于警醒误入歧途的“恋爱脑”女性,而其余更深层次的“真实”,则被挡在了温馨又悬浮的欢乐颂之外。
虽然知道不真实,但抱着娱乐的心态打发时间倒也无妨,久而久之,观众与悬浮剧达成了一种“默契”。除却资本的因素,这其中,又是否有你我的一份妥协?当社会话题变成电子榨菜,以虚拟的方式犒劳每一个现实中的都市丽人,而自身处境难以改变的丽人们,又自掏腰包为精神爽剧添砖加瓦,这种红利的“吃法”,似乎变成了一个无解的循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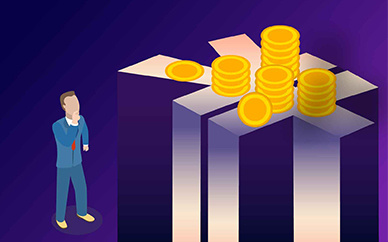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