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关注:《我是哪一个》:“遇见自己”的谜题与困境
 【资料图】
【资料图】
近日在北京大华城市艺术表演中心上演的《我是哪一个》,是易立明导演的“医学的胜利”三部曲之一,由英国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编剧。这是一部游走在谜题与谎言中、通过克隆人故事展现人类伦理困境的剧作。出于不明确的原因,父亲萨尔特同意用大儿子的基因克隆了小儿子,不想进行这项医学实验的医生私自克隆了更多的克隆体。当他们与同样的自己遭遇时,戏剧发生了。
“遇见自己”,如果没有孪生兄弟姐妹的话,那一定是一件令人惊恐的事儿。戏一开场,小伯纳德即遭遇了这种惊恐。他遇到了“一群”自己。父亲不得不告诉他——他是被用大儿子伯纳德的基因克隆出来的。而父亲只想克隆“一个”,未曾想医生竟然偷偷克隆了“一群”。于是,谜题出现了:父亲克隆儿子的动机是什么?父亲的解释是:大儿子四岁时与妈妈一起死于车祸,为了能再次“抚养”已死去的大儿子,他同意了克隆实验。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父亲的解释越发不能自圆其说,不断出现的叙事漏洞让父亲的动机扑朔迷离。
谎言就在父亲动机的谜题中诞生,并伴随解谜全过程。尤其当大儿子出现后,父亲的克隆动机就更难解释了。按照父亲的说法,克隆的原因是因为大儿子完美。显然,小儿子成了大儿子的替代品。那么,父亲爱的到底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恐怕不是小儿子。
然而,事实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大儿子并没有死。大儿子揭穿了一个真相:妈妈并非在他四岁时死于车祸,而是在他两岁时死于自杀。他四岁时,的确有一件大事发生——被父亲送进了福利院。在大儿子对父亲的质问中,新的问题产生了:既然大儿子是完美的,父亲何不留大儿子在身边?为什么要克隆一个小儿子,抛弃大儿子?从大儿子对童年记忆的复述中,我们发现,当年父亲并没有那么爱他。在他从妈妈自杀到自己去福利院的两年里,父亲基本无视他的存在。即便我们将父亲的反常态表现看作是家庭变故的结果,而后试图重新做一个称职的父亲乃源于忏悔之心,依然不能解释父亲的克隆动机。因为如果父亲想要弥补自己失职的过错,满可以从福利院接回大儿子,何必再造一个小儿子?所以,父爱不是理由。就算是爱,父亲爱的到底是哪一个?恐怕也不是大儿子。
父亲爱的是哪一个?“我”又是哪一个?这是一个关系到个体的唯一性和价值感的问题。因为不断的发现与否定,追问便尤为迫切。父亲自我譬解的克隆动机被大儿子否定了。那么,父亲为什么同意克隆小儿子?是否仅仅为了一个医学实验?如果是,这个医学实验对父亲意味着什么?他从中获利了吗?剧作开篇,我们看到父亲有强烈的“发财”冲动,有与医生打官司的计划,还生出一个克隆体值多少钱的设想,这让他当初克隆小儿子的动机显得极为可疑。不过,关于父亲的克隆动机,剧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留下引人遐思的空间,在充满漏洞的解释与自相矛盾的事实中,让难以解释的谜题和解释过程中的谎言,以纠缠不清的姿态共同指向克隆人类的伦理困境。
如果人类“遇见自己”,如何面对同样的自己?每一个个体人作为“人”的唯一性何在?“一模一样”与“不一样”的分野是什么?当“新的自己”出现,“旧的自己”是仅仅被复制还是已经被替代?当生物界的自然进化规律被破坏,人类如何相处和自处?这些问题无一不关涉科学与伦理的关系。虽然作品并没有直接去讨论这些问题,但小伯纳德的惊恐、大伯纳德的愤怒,大伯纳德杀了小伯纳德后自杀的突变,已然显示了这种困境的后果。但剧作家还觉得不够。她又用第三个克隆体布莱克的维度显示了另一种恐怖。身为三个孩子父亲的数学老师布莱克自得其乐地生活着,丝毫不介意自己是克隆体。这种“无脑”状态对父亲萨尔特构成的刺激,甚至超过大小伯纳德之死。因为放弃对个体人的唯一性、独特性的体认和追求的布莱克,某种意义上已不具备“人”的本质需求与特征。这恐怕是克隆人类更大的伦理困境。
在谜题、谎言和困境中,《我是哪一个》的台词充满隐含信息。人物间对话遮遮掩掩,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父亲和三个儿子间的相互试探多以半句话形式出现。他们要么会自己吞下后半句,要么话一出口即被对方打断或否定。而他们又会不断重复对方的话,只是经过重复后,同样的话又会产生新一层意思。因此,剧作大多台词都富含了潜台词。半句话、停顿和重复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戏剧节奏。舞台上,人物在你进我退间相互猜测;舞台下,观众则在思索玩味中默默推断。
配合剧情,作品的舞台呈现既是写实的,又充满象征意味。虽然客厅、浴室的舞台布景充满生活实感,但每到换场,舞台上小电视机里的画面便富于深意了。从黑白到彩色,电视里循序播放出现代战争炮火连天、军工企业制造武器、电气化时代标志性发明、电子化时代科技成果、人类精子自由畅游等画面,不由引起观众对于科技进步成果可否被滥用、被滥用的科技成果是否会反噬人类等问题的反思。剧终时,奔涌的白雾和冷色彩光制造的洪水滔天情境下,装满玩偶的浴盆缓缓升起,悬空停住。这个类似电影空镜头的定格,似乎在问:人类能否逃过劫难,走出困境,登上属于自己的诺亚方舟?(谷海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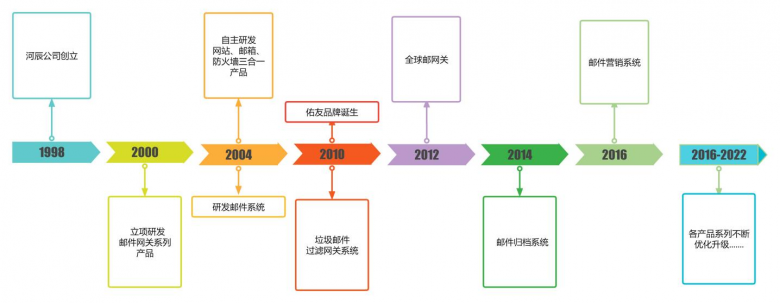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